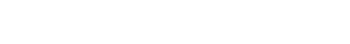植物提取物对畜禽免疫系统的影响:异喹啉生物碱模型(二)
发布时间:
2021-05-19
来源:
黏膜免疫系统的作用
肠道是直接与食物抗原、病原体、毒素和共生菌接触的人体最大的器官。肠上皮是由肠细胞、产生粘液的细胞(即杯状细胞)、产生抗菌肽的细胞(即潘氏细胞)和产生激素的细胞的四种分化的细胞类型组成的第一道防线。在上皮之下,固有层由免疫细胞组成,包括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它们负责先天免疫反应。树突状细胞能够通过插入到肠细胞之间的特殊胞浆延伸从肠腔中采集抗原,并将抗原呈递给固有层和淋巴结的T细胞和B细胞。这种相互作用代表了肠道先天免疫反应和适应性免疫反应之间的密切联系(Santaolalla等,2011年)。
炎症被定义为“血管化组织对感染和组织损伤的反应,炎症反应是将宿主防御的细胞和分子从循环系统转移至感染部位”(Kumar等,2015年)。
在应对病原感染和组织损伤时,炎症反应是最重要的非特异性先天免疫反应。先天免疫细胞可以通过位于细胞表面和细胞内的模式识别受体(PRRs)来识别组织损伤和病原体入侵。(Mogensen, 2009).
与身体其他部位一样,肠道中的炎症反应也始于PRRs的激活,如肠上皮细胞和固有层免疫细胞中的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s)。众所周知,转录因子NF-kB在肠道炎症反应的启动,促进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产生,以及炎性细胞的募集中起着关键作用。
一旦PRRs被触发,一个信号级联就会启动,以促进白细胞向受损/感染区域的募集。信号级联涉及多种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刺激分子的产生和释放,它们在血管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增加血液流速和血管通透性,并确保炎症细胞粘附和迁移到炎症部位并随后激活(Newton和Dixit,2012)。炎症反应的介质包括前列腺素、组胺、一氧化氮(NO)和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TNF)和白细胞介素1(IL-1)。激活的白细胞(包括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可以消除损伤因子,并修复受损的组织。此外,激活的白细胞会产生促炎和抗炎两类细胞因子,以放大和调节炎症反应,并介导适应性免疫反应。此外,细胞因子促进急性期蛋白(APP)的产生,这将对免疫反应产生系统影响。(Newton和Dixit,2012)。
NF-kB信号通路的作用
PRRs的一个常见信号发生是转录因子NF-kB的激活。众所周知,NF-kB在炎症反应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NF-κB的激活诱导了促炎基因的转录,即编码促炎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 (Tak和Firestein,2001)。正常情况下,由于被抑制性蛋白(如IkB家族蛋白,主要是IkBα)所结合,NF-κB在大多数细胞的胞浆中保持非激活状态。NF-kB的典型激活涉及微生物分子和促炎细胞因子(如IL-1和TNF)对PRRs的刺激(Newton和Dixit,2012)。病原模式识别受体(PRRs)激活后,通过促进IκB激酶(IKK)复合物的磷酸化来促进IkBα抑制蛋白的降解,进而导致NF-kB移位到细胞核并启动促炎基因的转录(Liu等,2017年)。因此,促炎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粘附分子的产生增加。此外,NF-kB转录因子的激活还参与调节细胞增殖、细胞凋亡和细胞分化(Liu等,2017年)。
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释放会导致机体发生局部变化(即发热、发红、疼痛和水肿)以及全身性变化。炎症的系统性后果包括肝脏中急性期蛋白(APP)的合成和释放,如C反应蛋白、血清淀粉样蛋白A和结合珠蛋白,一氧化氮合酶和其他参与糖异生和糖原分解相关酶的激活以及胰岛素抵抗。此外,还观察到包括厌食症和嗜睡在内的行为变化。炎症引起的神经内分泌变化促进发烧以及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的释放(Gabay和Kushner,1999)。此外,还观察到包括厌食症和嗜睡在内的行为变化。炎症引起的神经内分泌变化主要是体温升高以及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的释放增加(Gabay和Kushner,1999)。
肠道炎症的起因及危害
众所周知,肠道病原体是导致肠屏障功能障碍的原因(Berkes等,2003年)。细菌及其毒素可通过影响紧密连接蛋白的形态和结构直接改变肠上皮细胞的完整性,并通过导致肠道炎症而间接改变肠上皮细胞的完整性。病原体及其毒素并不是导致肠道炎症的唯一原因。饲料成分和饲料中的非营养成分也可以触发免疫系统,启动炎症的级联反应。
复杂的炎症反应过程被机体严格的调控,以确保损伤因子得以及时消除,受损组织得以及时修复。然而,如果这种调控失效了或者导致炎症的原因持续存在,则可能对动物的健康和生长性能造成有害影响。实际上,NF-kB的失调与人类慢性炎症状态有关,例如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Berkes等,2003;Nanthakumar等,2011)。
启动免疫反应,甚至维持预警的、反应迅速的、受到控制的免疫系统,是一个营养需要的过程,需要营养素的重新分配(Lochmiler和Deerenberg,2003)。换句话说,建立一种免疫反应,即使是温和的,也需要利用本可以用于其他生理过程的营养。在免疫反应过程中的这种营养分配模型,是动物生长、繁殖、体温调节以及免疫之间协调的结果(Sheldon和Ver-Hulst,1996)。
急性期免疫反应早期的代谢特征是高代谢状态和蛋白质营养不良(Lochmiller和Deerenberg,2003年)。促炎细胞因子,包括IL-1,TNF和IL-6均可引起厌食。因此,身体必须利用自身的储备为免疫系统提供必要的营养和能量。在骨骼肌中,蛋白质被降解(蛋白水解),蛋白质的合成减少以增加氨基酸的利用率,这些氨基酸将在肝脏中用于合成葡萄糖作为能源,这个过程称为糖异生。同时,糖原和脂质也被降解(即分别为糖酵解和脂肪分解)以产生更多的能量供给免疫系统(Lochmiller和Deerenberg,2003年)。如果炎症持续,则动物的体重会降低,身体状况下降。Mercier等(2002)研究表明,在慢性肠炎模型下,肌肉中的蛋白质合成减少了23%,但是,由于急性期蛋白的合成和受损肠细胞的置换,肝脏和肠道中的蛋白质合成分别增加了63%和19%(Mercier等,2002)。
此外,肠道炎症还伴随着吸收不良,这进一步限制了能量和营养的可获得性。吸收不良可能是由于细菌过度生长和肠道炎症引起的肠上皮结构改变所致。众所周知,肠道炎症通过改变紧密连接对肠道屏障功能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导致“肠漏”综合征。此外,体液和电解质被分泌到管腔,导致腹泻和吸收不良(Berkes等,2003年)。
炎症导致的生产成本提高很难准确预测。但有研究表明,猪的轻度免疫反应使增重和采食量分别降低21%和15%(Spurlock等,1997)。在鸡中,肠道炎症导致增重减少13%-18%(Klasing等,1987)
慢性炎症对动物生产性能有负面影响。因此,具有局部抗炎作用的草药和植物提取物在畜牧业中受到极大关注。调节过度的肠道炎症可降低免疫反应的营养消耗,并将更多的营养素用于动物生长和生产,以及通过维持更健康的肠道屏障功能而减少肠道疾病的发生。
具有抗炎特性的植物代谢物
植物提取物通常指可以通过溶剂处理从植物组织中提取的物质或化合物。基于植物次生代谢产物(SMs)表现出的抗炎活性,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是植物提取物应用目的之一。
依据分子结构,植物次生代谢产物(SMs)可以分为含氮和不含氮两类。含氮次生代谢产物主要包括生物碱,非蛋白质氨基酸,糖苷,芥子油苷,胺,凝集素和肽,无氮次生代谢产物包括:萜类,酚类,聚乙炔,碳水化合物和有机酸(Wink,2015)。
植物次生代谢产物(SMs)对植物的生长和发育无支持作用,但在植物防御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为植物生存所必需。植物次生代谢产物(SMs)具有许多特征,例如抗微生物,抗氧化,抗真菌,抗病毒,抗癌和抗炎(Osbourn和Lanzotti,2009年)。
无氮次生代谢产物
多酚是一种主要由天然有机化合物组成的结构基团,其特征是存在大倍数的苯酚结构单元。植物多酚在植物分布和植物丰富度、环境因子对植物丰富度的影响,植物之间及植物与其它有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黄酮类化合物是多酚中最大的一类,其特征是有两个带有酚羟基或甲氧基的芳香环。此外,它们通常以糖苷形式出现,储存在植物细胞的液泡中(Kabera等,2014年)。黄酮类化合物可分为六个亚类:黄烷醇(如:儿茶素、没食子儿茶素)、黄烷酮(如:橙皮苷、柚皮素)、黄酮(如:叶茶素、芹菜碱)、黄酮醇(如:槲皮素、山奈酚)、异黄酮(如:染料木素、大豆苷元)和花青素(如:花青素、橙皮素)。需要说明的是术语“单宁”被广泛应用于任何含有足够的羟基和其他合适的基团(如羧基)的大分子量多酚化合物,以与各种大分子形成强烈的络合物。受植物品种和使用部位,以及栽培、收获和加工条件的影响,食品和饲料中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所不同。
生物利用度是一种药理学指标,其描述了一种物质达到系统代谢不变后被潜在的靶器官或组织中利用的量(Aktories等,2013)。
物质的生物利用度主要受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的影响,而黄酮类化合物之间的生物利用度存在巨大差异。例如,类黄酮糖苷(非糖基化分子)在单胃动物中的吸收要优于反刍动物(Beyer,2015)。由于大多数植物类黄酮(黄烷醇除外)都被糖基化了,因此必须先用酶将这些分子水解后才具有可利用性。黄酮类化合物的系统利用率还取决于肠道上皮的吸收,粘液分泌强度以及胆汁的分泌。
在动物体内多酚化合物会快速降解并排泄。由于瘤胃微生物的全面降解和调节的影响,反刍动物中黄酮类化合物的可利用性与单胃类相比有所不同。体外研究表明,黄酮醇化合物槲皮素具有较好的抗炎作用。槲皮素可以清除活性氧和活性氮基团,并对促炎信号通路(如:NF-kB和MAPK)的酶具有抑制作用(Fürst和Zündorf,2014)。
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GCG)是绿茶儿茶素家族中最著名的成员,由于其分子大小,其在饲料和食品市场上绿茶类产品中的含量最多。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GCG)具有很好的抗炎,抗氧化,抗感染和抗癌作用。EGCG通过影响细胞周期调节蛋白和抑制NF-kB信号通路,抑制生长因子依赖性信号传导,蛋白酶体依赖性降解,MAPK途径和COX-2的表达,进而诱导细胞凋亡(Fürst和Zündorf,2014)。
另一类具有抗炎特性的物质是植物精油(EOs)。植物精油具有复杂的化学组成,由十几甚至上百个化合物不等。植物精油中鉴定出的大多数成分主要是萜烯类(氧化或非氧化)化合物,其中主要是单萜和倍半萜。另外,植物精油中烯丙基和丙烯基苯酚(苯基丙烷)也是很重要的组成。
植物精油在国际上被定义为将植物或其相应部位通过蒸馏或适当不加热的机械方法获得的产品(Miguel,2010)。植物精油是碳氢化合物及其氧化衍生物的复杂混合物。自古以来,由于其生物活性,植物精油在全世界许多不同的传统治疗系统中使用。植物精油可以清除自由基,也可以充当抗炎药,因为多种细胞(单核细胞,嗜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氧化损伤也会诱发炎症反应。许多临床前研究已经证明了精油在几种细胞培养和动物模型中的抗微生物,抗氧化剂,抗炎和抗癌活性(Miguel,2010)。
体外试验已经证明植物精油及其化合物具有抗微生物,抗氧化,免疫调节和抗炎功效(Miguel,2010年),可能对肠道炎性疾病具有保护作用。例如,洋甘菊精油作为抗炎药已使用了几个世纪。植物精油的抗炎活性不仅可归因于其抗氧化活性,还以归因于其与涉及细胞因子和调节转录因子的信号级联反应的相互作用。同样,植物精油影响促炎症基因的表达也可预见(Miguel,2010)。
植物精油在动物饲料中的应用效果受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一方面可能是日粮中不稳定成分和日粮中植物精油的不同水平;另一方面可能是动物的遗传因素(HüsnuCan Baser和Buchbauer,2009)。
含氮次生代谢产物
生物碱是以氨基酸为底物通过天然生物合成的含氮化合物。然而,并不是所有(但大多数)生物碱都具有基本结构特征,即至少包含一个环状结合的氮,具有反应性的碱性并显示出生物活性。
生物碱是最大的天然产物类别之一,在植物防御食草动物和其他种间防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物碱化合物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功能,可以防止食草动物和微生物的侵袭,并可以作为传粉媒介和种子分散者的引诱剂。植物体内的生物碱化合物可通过抑制邻近植物物种的生长而促进植物的竞争力和入侵力增强,这种特性也称作化感作用(Osbourn and Lanzotti,2009)。其中有些生物碱是植物抗毒素,抗微生物剂,通常是抗氧化性物质,它们在病原体感染区域内迅速积累。生物碱还可作为花色素的强化元素,作为激素和信号分子吸引授粉媒介子。最后,生物碱化合物是新药和植保产品开发的潜在替代品(Osbourn和Lanzotti,2009年)。
除了吗啡,可待因,辣椒素,胡椒碱和奎宁,还有一系列具有特定功能的生物碱,它们几乎可以无限扩展。Adaline与Propylein是瓢虫分泌的二种有防御作用的生物碱;蜥蜴碱是由火蜥蜴分泌的甾体生物碱;仙人球毒碱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仙人掌中的药物;大麦产生的芦竹碱可作为色氨酸合成的基本原料;阿托品生物碱存在于自然界茄科植物的许多植物中,并在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目录清单中;血根碱、白屈菜红碱、原阿片碱、别隐品碱由罂粟科博落回植物产生(Kosina等,2010年)。
博落回在许多出版物中都有描述,并一直作为传统中药使用。众所周知,博落回具有抗微生物,抗菌和抗炎等生物活性,并且现代研究表明博落回可以通过诱导细胞凋亡发挥抗癌作用。最后,博落回作为饲料添加剂已经在全球广泛应用(Zeng等,2013)
植物,炎症,细胞,反应,肠道,化合物,具有,免疫,精油
最新新闻
万众“溢”心 再启征程 | 世唯科技2025年工作动员暨聘任大会圆满举行
2025-02-08
2024-12-24
2024-11-06
2022-06-14
2019-02-19
金蛇贺岁 共赴美好 | 2024奥门原料免费资料举行2025年开工仪式
2025-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