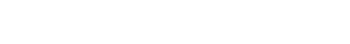2014年,“洋草药”在大陆的销售额约为50亿元,约占国内中药销售额的1%,但德国银杏类制剂等产品已具备品牌优势。 青蒿素是我国唯一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基本用药目录的药物,却被外国同类产品申请了专利。目前国际市场上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年销售额高达15亿美元,中国的市场占有量不到1%。“土生”的植物药,尴尬地成为了国外药厂的摇钱树。作为一名母亲,吴铭萱(化名)最近有些纠结。纠结源于一盒德国进口草药“施保利通片”,这是2岁儿子的抗病毒感冒用药,国药准字Z字头注册号,成分侧柏叶、赝靛根、紫雏菊根。“含紫雏菊的药物制剂可引起皮疹、发痒、罕见面部浮肿、呼吸困难、头晕和血压下降”,说明书上的副作用让她有些迟疑。她在微博上向某知名药师求助,希望能得到药片能否用于2岁宝宝的答复。没想到,却有陌生人留言,“去看看德文版说明书”。随着全球回归自然理念的兴起和健康观念的变化,像施保利通片这样的天然植物药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作为不少中药的原产国,我国中药企业的“后院”却在遭遇“洋草药”的蚕食。跨国药企将目光瞄准中国市场,纷纷抢滩登陆。“洋草药”返销儿科医生、广州和睦家诊所医疗总监夏凯莉能感觉到,这些年,“洋草药”的处方在一些公立医院越来越常见。头顶“进口药”的金字招牌,“洋草药”备受年轻家长青睐。尽管一直对其有效性持保留意见,但夏凯莉承认,至少在味道上,它们比传统汤剂中草药更容易接受。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以下简称医保商会)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前7个月,包括中成药、中药饮片、提取物在内,我国中药进口额约为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微增1.7%;出口额约为22.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中药出口中,植物提取物占比最高,达57%。医保商会副会长刘张林分析,这是中药材粗加工后附加值较低的中药产品,德国、日本、韩国等国进口后,一部分被用作进行中药产品深加工,变成地道的中成药,其附加值最高可升至几十倍。2014年,为研究“洋草药”返销大陆的情况,医保商会专门在北京和一些省份的医院和药店做了一次调查。据不完全统计,“洋草药”在大陆的年销售额约为50亿元。“没有想象中的来势汹汹,只占国内中药销售额的1%,但德国银杏类制剂等产品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和品牌优势。”刘张林表示。在他的印象里,“洋草药”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进入中国大陆。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欧洲和日韩等跨国制药公司通过在华投资、并购中药企业等策略,“洋草药”抢滩中国开始提速。事实上,跨国药企早就尝到过中药领域的“甜头”。上世纪90年代,瑞士诺华曾与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合作开发了专利中药复方蒿甲醚,从而使诺华在世界抗疟疾药物市场跃居前列。在中科院院士、全国药用植物及植物药专业委员会顾问孙汉董看来,跨国药企进军中药领域,是看中了13亿人口的潜在市场,更是看到了中医在治疗慢性疾病方面的优势。“中医的整体观和全局观、标本兼治和辨证施治的理念与当今西方医药发展的思路高度吻合。”孙汉董说,随着人们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的改变,疾病谱已悄然发生变化。对于心脑血管疾病、代谢障碍性疾病、肿瘤来说,这些疾病不是针对一个单独的靶点治疗就可以解决的。在这些领域,中药因为多靶点治疗,具有独特的优势。草药出国先办护照想要进入海外市场,必须先办理跨出国门的“护照”,“洋草药”首先需要通过严格的注册审查。尽管欧洲草药用药的历史可追溯至古希腊,超过60%的欧洲人使用过草药,但长久以来,草药只能以食品和保健品的形式在欧洲销售。1991年,一群比利时女性在服用含有马兜铃酸的减肥中药后,出现肾功能损伤。105例病例中,其中超过三分之一进入晚期肾衰竭阶段,不得不接受肾移植或透析治疗。一时间,欧盟各国对植物药严阵以待,如何保证用药安全被提上日程。最终,欧盟决定对植物药“网开一面”。2004年4月30日,欧盟颁布《传统植物药品注册指令》(以下简称指令),规定在长达7年的过渡期内,那些具有悠久使用历史的草药,只要满足条件,就可以通过简化注册程序成为药品。“一是欧盟内连续30年,或欧盟内15年欧盟外30年的用药安全性及效果证明;二是残留物、微生物含量等生产规范标准。”欧洲草药产品委员会主席温纳·克诺斯(WernerKnoss)介绍,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就可免做临床前及临床试验。在2011年5月1日“大限”过后,植物药可以通过“传统应用注册”“固有应用注册”或“独立/混合申请”三种方式注册。“不管采取哪种注册方式,药品质量必须要过关。”欧洲药品管理局媒体与公共关系部负责人埃拉尼·费斯蒂卡奇(EleniFistikaki)强调。在孙汉董看来,“洋草药”之所以受国人青睐,和严格的质量标准密不可分,“这是洋中药最大的倚仗,却恰恰是我们的软肋”。他直言,目前我国很多中药产品的品质并不十分稳定,同一款中药,不同厂家生产的产品、同一厂家生产的不同批次的产品,由于原料、指标控制的不同,疗效差异会很大。“欧盟在农药残留、重金属污染检测方面的标准确实要比《中国药典》高。”这是受访专家较为一致的看法。在中国,中药材大多来自种植散户。由于缺乏指导,散户的种植和病虫害防治技术普遍落后,需要更多地依赖化肥和农药,农药残留和重金属不符合国家标准。但在检测方面,企业却面临着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药材的含量测定是保证植物药质量的关键。”克诺斯表示,《欧洲药典》中收载的植物药和植物药产品均有相应的有效成分含量限度标准,使用色谱法测定有效成分的含量。除了《欧洲药典》,2004年后,克诺斯所在的草药产品委员会还陆续制定出了一系列指南,对药品质量、安全性、有效性进行了细化。在通过本国注册批准和上市许可后,“洋草药”想要进入中国,还必须符合中国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经国家食药监局和审评中心评审后,对于符合质量标准、安全有效的,核发《进口药品注册证》。被抢注的专利2014年9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一组数据让不少业内人士倍感担忧——我国是中草药大国,但有九百多种中草药已被外国公司抢注了专利。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医药生物发明审查部负责人当时的介绍,很多中药配方被欧美、日韩等国获取,并在国外甚至我国境内申请专利,“以日本为例,其210个汉方药制剂的处方都来自中国”。“洋草药进入中国市场,和国内企业专利意识薄弱有一定的关系。”刘张林表示。最典型的代表是青蒿素。这是我国唯一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基本用药目录的药物。从1978年研制成功至今,它已让数千万疟疾病人免于死亡。但由于当时中国缺乏专利保护意识,多次在学术杂志、国际大会上详尽地公布青蒿素的化学结构、药效、临床资料等,没过几年,外国同类产品便陆续问世,并申请了专利。资料显示,目前国际市场上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年销售额高达15亿美元,但中国的市场占有量不到1%。“土生”的植物药,尴尬地成为了国外药厂的摇钱树。而在孙汉董看来,除了对知识产权保护无力,申请专利遭遇标准化难题也让本土中药饱受“洋草药”的冲击。本土中草药专利保护难,背后有着说不出的痛。中药饮片或制剂中,一种药往往含有十几味甚至几十味药材,有效成分和组分很难检测清楚。不良反应的临床检测是中药产业中最为缺乏的环节之一。一些企业或许是担心标注不良反应会引起患者担心,从而缩小药品的适用范围,对标注不良反应的积极性不高。孙汉董表示,不仅如此,很多中成药上市太快,缺乏充分的大规模临床试验数据是业内的普遍现象。缺乏有说服力的数据,尽管疗效显著,但药理却难以验证,专利保护就如同沙上建塔。“外资药企敢于进军陌生的中药领域,就在于他们抓住了本土中药研发的要害所在,利用自身科技实力实现中药的现代化生产,搞清成分机理并申请专利。”孙汉董认为。不过,对于眼下“洋草药”的强势来袭,孙汉董并不担心。从规范中药企业的标准、分析药物疗效并稳定质量的角度而言,他甚至觉得利大于弊,“竞争不是什么坏事,有竞争才会有创新”。来源:南方周末
【听课笔记】中兽药、饲用植物提取物标准与应用——曾建国教授报告实录
专家简介 曾建国,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兽用中药资源与中兽药创制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中药材生产(湖南)技术中心主任、国家植物功能成分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报告实录 中兽药 中兽药是指是指以中药材为原料制成的用于动物疾病防治与提高生产性能的药物。其成药原则有以下几条: 安全:对靶动物使用安全;药物残留及代谢残留物安全;鉴于养殖业群体饲喂的特殊性,对于用于长期添加的药物饲料添加剂而言,还要关注对环境的影响。 有效:对大部分生命周期在半年以内甚至几十天的养殖动物病患有较为显著的治疗效果,或在预防疾病与改善生产性能上有较显著帮助。 可控:作为商品其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是可以控制的。 低成本:在上述三点的基础上,中兽药作为养殖经济服务的商品,其成本是考量市场价值的主要指标。 此外,还要注意药物开发和应用的区别。在开发兽药时的有效剂量和应用时的有效剂量并不相同,生产实践中的使用剂量往往相对更低,如何在此情况下保证效果?有些厂家会违规添加其他物质,极大地伤害产业。因此,开发时一定要注意使用成本,使实际效果与研究成果保持一致。开发中兽药时,应慎用贵重药材,不与人药争夺资源。 功能性饲用植物产品替代抗生素 抗生素的替代逐渐受到重视,但“替抗”专指替代“饲用抗生素”应用的保健预防和促生长、可长期添加到饲料中的使用途径,而绝不是指替代抗生素抗感染在动物治疗作用。开发兼具“治未病”(保健)、“促生长”(营养)的双重属性的功能性饲用植物产品大有前景。 国家规定了可使用的饲用植物,但并未制定相应的标准,这使得生产实践中隐藏着漏洞。检验方法缺失,使得质量好坏无从判别,以次充好、造假泛滥而没有判断标准;功能不明晰,使得指导添加应用缺乏依据,添加量与效果缺乏数据,成本与市场之间存在矛盾。 饲用植物提取物(及粉末)标准体系建立在两个标准、三个规程上:药材标准和终端产品标准;原料SOP,工艺SOP,检验SOP。满足了两个标准、三个SOP的产品才是标准化的产品。这样可以避免出现植物使用部位、收割时期、加工工艺、检验方法差异带来的质量差异,保证产品效果一致。 值得关注的活性物质 以下几类用于饲料添加剂和药物饲料添加剂的成分值得关注: 精油、挥发类,如牛至油、紫苏油、脂溶性色素等; 生物碱类,如血根碱; 有机酸,酚类,如异绿原酸(源自甜叶菊),鞣质多酚(如五倍子)。 注:以上内容根据会议现场录音整理,如有疑问请联系赛尔传媒。 文章来源:赛尔畜牧网
来源:环保部主办《环境教育》杂志作者:蒋高明 本文发表于环保部主办《环境教育》杂志,2015,(8):814 自2005年以来,身为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的我,带领一批批研究生一直在自己的家乡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进行生态农业实践,承包了约40亩低产田,办了一个生态农场。我们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很多变化。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这10年的生态农业实践中,中国农村的污染问题不但没有改观,反而越来越严重。由于普遍采取了违背自然规律的生产模式,同时城市垃圾大量进入农村,发达地区淘汰的产业在落后农村落地,因此,农村中出现了多种污染。本文章所反应的问题,是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的真实现状。 调查之一:令人窒息的臭味 2015年7月,山东几省连遇高温,部分城市达到40度。在这样高温天气下,一些化工厂、养殖场散发的臭味令人窒息。 在我的生态农场西北角,两年前出现了一个非法养殖场,属于工厂化养鸭,鸭子从蛋壳出来到长大25天即可以出笼。在其上游就有一个规模化的屠鸭厂。屠宰后的鸭子进入到南方城市,被一些不知情的消费者吃掉了。经济发达的地方,为转移污染,将工厂化养殖场和屠宰厂转移到了经济相对落后的沂蒙山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里恰好位处水源地上游,这里的污水与生产的垃圾食品又回到了他们的餐桌。 臭气来自养鸭场的鸭子粪便,平时气味就很大,再遇到到高温,臭气浓度增加几倍,臭气熏天。尽管政府规定畜禽粪便要干湿分离,不准冲洗,但这些黑心养鸭场不管不顾,照样用水冲,不仅严重污染了周围河流,在冲洗过程中还添加了大量火碱,这样的鸭粪不仅不能肥地,还会烧死庄稼。 之所以25天鸭子就能够出笼,得益于大量使用饲料添加剂,各种重金属、抗生素、激素都添加到饲料里面,让鸭子异速增长。不要说这样的鸭肉存在严重的质量安全问题,就连粪便都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长期在鸭场工作的农民也有健康隐患。 最近临沂市在铁腕治污,希望借此春风,对于存在偏远农村的严重违背自然规律、严重污染生态环境的养殖场予以清理,早日还沂蒙山人民久违多年的绿水青山。 调查之二:地下水不能喝了 我们在农村调研,发现买水喝的农民越来越多了。最早发现农民买水喝是2013年春节前后,今年村民发现买水喝已成为普遍现象。沿沂蒙山金线河两岸的十几个村庄,当年都是到河边沙滩取水喝,或者每个村里都有井,喝的就是浅层地下水。如今,河里的水早就不能喝了,现在井水也不能喝了,连镇上供应的自来水也几乎不能喝了。 有条件的家庭花钱打深水井,打井变成一个产业。 河水不能喝是沿河工业尤其屠宰业、工厂化养殖业造成的,河水已严重污染,成了劣五类水;浅层地下水不能喝是农业污染惹的祸,农民为图省事,减少向土地上投入,使用大量的化肥、除草剂等农药,最终导致了赖以为生的地下水不能喝了。原本喝水不要钱的农民,今天尝到了花钱买水喝的苦头——那水是要天天买、顿顿买的啊。 水是从山上买的,村庄的上游就是蒙山,蒙山由于植被覆盖好,少农田,所产生的水干净还有一丝丝的甜味。然而,几年前我去考察,发现那里的水源也面临着污染隐患。由于游人增多,山上遍布各种农家乐餐馆,餐饮业的废水直接排放到水源中去。 农民向环境中使用了多少化肥农药?一般一亩地三四百斤化肥,两三斤农药,这些化学物质,能够被利用庄稼或保护庄稼的,占10%~30%,也就是说大量化学物质是用来污染的,污染的比例高达70%~90%。大量化肥、除草剂等农药、地膜造成土壤污染和土地肥力的严重下降,土地肥力下降又带动了农药化肥产业兴旺。政府在源头补贴化肥、农药、农膜等,以至于这些化学物质非常便宜,使用起来连农民都不心疼——农民除一亩杂草,除草剂的费用仅为2.1元! 调查之三:害虫越杀越多 进入7月,调查区平邑县卞桥镇石桥、南安靖、卞桥、西荆埠、黄埔庄等几个村子的农民开始忙碌起来。农田里爆发了一种钻心虫,专门啃食玉米芯,即顶端的幼叶,吃完后就钻到植株下面的部位,非常难以治理,农民恨之入骨。 农民每年都要向地里打多遍农药,加上播种期用农药拌种,使用农药四五次属于正常,如果种植果树,每年打药的次数高达20多次。 现在的农田充满了杀机,害虫几乎都是经过农药洗礼的,农药越用越多,而害虫似乎也越战越勇,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人虫大战中,化学对抗的胜者似乎是害虫而不是人类——医院里癌症病人越来越多,而害虫繁殖速度依然成倍增长。 害虫在农药胁迫下,会出现进化,这个进化是在农药诱导下产生的。据说有些害虫泡在农药原液里也毒不死。这类害虫进化出来了一层隔离液态的蜡质毛。如果有人研究农药诱导的害虫进化机理,应当有很好的科学发现。农民不知道其中的原理,每年继续有成吨的农药倾倒在农田里。 有些虫害是农药商和农药贩子人为制造出来的恐慌,为了吓唬农民,其目的是兜售其农药,他们不关心农民是否治住了害虫,他们关心的是农药的销售量。 当农田出现的害虫的时候,仅仅是每亩出现2~3头害虫的时候,植保专家就建议农民喷洒农药,还推荐他们使用哪一种农药。如果不打,农民们经常听到的是下面的话: 你不打农药吗?不打庄稼都毁了。 一些政府官员也成了农药商的传话筒:“不打农药,产量会减少70%,甚至会绝产。” 现在农药的名称越来越奇怪,如“一步绝”、“一月无虫”等,既充满了对害虫咬牙切齿的恨,又充满了对农民的诱惑——不怕你不来买。 调查之四:河流变成臭水沟 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村的东面有一条小河,叫金线河,是沂河的上游。沂河是淮河流域泗沂沭水系中较大的河流,从江苏入海。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沿河十几个村庄的村民就是靠这条小河生活,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面水都能喝,不需要进行水处理。这条河至今也是临沂市以及沿线城市的水源地,但需要进行各种水处理措施。 过去村里还没有空调的时候,这条河就是天然的避暑地。在炎热的夏季,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就是用这条河去除身上的热气,男人在上河洗澡;女人在下河洗澡,但男人的权利是白天和黑夜都能洗,而女人只有在晚上才洗。 村里人对这条小河有着很多的回忆: 河里有很多的鱼,夏天发洪水时可以在浅滩上抓到几十斤重的大鲤鱼,鱼是从上游水库里跑出来的,水流平缓时也能看到一些鱼儿在浅浅的水底下静静地呆着。有一种鱼,我们叫它“沙里趴”(学名沙鳢,鳢科鱼类),用手就能抓住,至于深水里的螃蟹、虾米、青蛙、泥鳅等就更多了。孩子们用笊篱就能捞虾,手巧的还会织渔网,并织成簸箕的形状,绑在长杆上,就可以抓到更多的鱼。小河再往远处流便是密不见人的森林,胆小的孩子是不敢走进去的。森林里有一种叫小黄雀的鸟,羽毛金黄,小而灵活,孩子们的弹弓很难打到它。一到夏天,数不尽的知了响彻整个森林,天气越热,叫得越欢,这时候,孩子们最高兴的事就是一下课就去粘知了,拣知了皮,逮知了牛(也就是金蝉,金蝉是蝉的幼虫,脱壳之后就成了蝉)。 今天,这条小河已经严重变臭,不能游泳,更不能喝了,水里的鱼虾没有了,沿河的芦苇荡没有了。这条河每天都要负重将各种污染物搬运到下游去,再经过沿线的城市,最终流向大海。 据村里人介绍,河水变质是从砍伐当地森林开始的,这个过程大约发生在1982年前后,首先是分了集体林,将多样化的当地森林卖掉分掉,然后种植上清一色的杨树。随后,人们发现了发财的机会——卖沙子。由于城市急剧发展,大量需要沙子,金线河的沙子被层层截挖,这里的沙子被制成混凝土,撑起了一座座城市。 后来,人们沿河疯狂建各种养殖场,大都是工厂化速生养殖场,养鸡养鸭,污水直排金线河;鸡鸭多了之后,于是就沿河建起了屠宰场,屠宰废水基本没有经过处理就进入了金线河。 还有其他大小工厂,以及农田里排放出来的化肥、农药、地膜的碎片,下雨的时候也随着地表径流进入了金线河。 这条曾经美丽的金线河,早在20年前就已经名存实亡了。现在山东乃至整个内地省份,已经很难找到沙子了。而底泥中的重金属等物质也需要专门的处理恢复,其代价的是昂贵的。 调查之五:垃圾包围农村 调查发现,农村中垃圾严重增多了,尤其白色污染。 倒退三四十年,乡村是很少垃圾的。那个时候没有塑料袋,也没有农膜,主要是动物和人的排泄物。勤快的农民都要将这些排泄物收集起来,放在猪圈里作为肥料。当年有一种农活就叫拾粪,几乎每一个农户家里都有拾粪的工具,沂蒙山人管一种棉槐条编的农具叫粪箕子,就与这种农活有关。 如今,人和动物的粪便明显比过去少见了,但严重增多的是各种垃圾。 首先,农田的地膜残留物就是一种。每年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如西瓜、花生、土豆等都需要大量使用地膜。这些地膜非常薄,没有回收利用价值,收获庄稼后农民就将地膜捡起来放在地头,一些残留的农膜留在地里。有时候地头上杂草多了,农民在烧杂草的时候,一把火也将地膜焚烧了,释放出严重的致癌物。 其次,是各种农药、化肥的包装物。它们几乎都是塑料类制品,有些为塑料袋,有些加工成塑料瓶。 第三是各种食品的包装物。饮料瓶、矿泉水瓶、牛奶瓶,方便面袋,薯条袋,几乎村民从商店里买来的所有食物都是用塑料包装的,即使香烟,外面也有一层膜。 第四是各种塑料袋。城里人的超市对塑料袋实施限塑令,但那些被限制的塑料袋全部进入乡村,现在农民赶集卖东西,根本没有带包带筐的习惯了,到处都提供一次性塑料袋。集市散场后,地面上的垃圾塑料袋遮盖地面,由于乡村没有专门的环卫人员,这些垃圾袋借助风或雨水的力量,就会进入河流或沟渠。 第五是村民的各种生活垃圾。旧衣服烂鞋袜,废旧的塑料桶,墩布头与塑料把,加上烂菜叶与废纸片,这些垃圾有些就手被村民倾倒在沟渠内,刮风下雨后再冲到下游去。 调查之六:得癌症的多了 蒋家庄的村民,第一次听说癌症这个词,是20世纪70年代。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去世,县有线广播里传来这个消息。村民们悲痛之余,私下互相打听,癌症是什么样的病,那么厉害,连国家都治不好。可见,40年前,癌症对于村民完全是很新的名词。 如今,村民们因病去世的多了,而更多的病,都是在医院里查出的癌症。先是村民感觉某个部位不舒服,疼痛难忍,送去医院检查,往往都是癌症后期。后来这样的事情多了,谁家发现有人疼痛,就很自然地猜想是不是得了癌症。